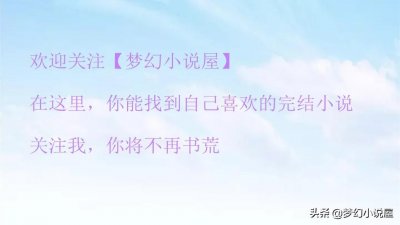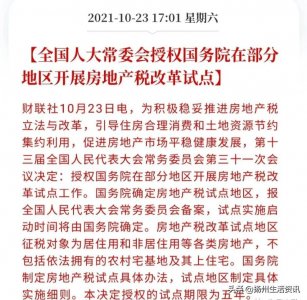昙花一现的草原霸主:薛延陀
早期隶属突厥
薛延陀出自匈奴铁勒部,而突厥政权兴起于6世纪中叶,其中铁勒就是被突厥所依赖的重要力量。《北史》称其“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铁勒“并无君长”,只是分散的一群大散沙,并没有整合起来,而分属东西突厥,可见铁勒实际上是处于被突厥帝国征服的状态。

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契弊、薄落职、乙咥、苏婆、那曷、乌护、纥骨、也咥、于尼护等,胜兵可二万。金山西南,有薛延阤、咥勒儿、十盘、达契等,一万馀兵。康国北,傍阿得水,则有诃咥、曷截、拨忽、比干、具海、曷北悉、何嵯苏、拔也末、谒达等,有三万许兵。得嶷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素咽、篾促、萨忽等诸姓,八千馀。拂菻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嗢昏等,近二万人。北海南,则都波等。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北史·突厥 铁勒》)
而铁勒“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实为游牧民族本色,加之“人性凶忍,善于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可见其人不仅残忍好杀,又懂得骑射,是极好的兵源,本来是柔然的附属,后来反叛柔然,柔然派兵进攻结果战败,而突厥却将其击破,“降五万余家”,之后突厥伊利可汗向柔然求婚,却被辱骂,于是本为柔然“锻奴”的突厥反叛,最终击灭柔然,成为草原霸主。如此一来铁勒又被突厥汗国统治者加以利用,“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
隋文帝开皇末年,由于突厥被隋朝利用分化政策加上已有矛盾陷入内乱,诸部离散,都蓝可汗被属部杀害,西突厥达头可汗在漠北自立为步迦可汗,而之后铁勒和突厥各部叛步迦可汗,步迦奔往土谷浑,不知所终。之后隋文帝扶持启民可汗北归,东突厥汗国复兴。大业元年(605),东突厥阿波系泥撅处罗可汗强盛,铁勒诸部都向泥撅处罗可汗称臣,但是泥撅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为变,遂集其魁帅数百人,尽诛之。”(《隋书》)如此残暴的行为,自然引起铁勒诸部的反抗,所谓“一时反叛,拒处罗”,可见此时铁勒起义规模之大。铁勒拥立“俟利发俟斤契弊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贪汗山,又立“薛延陀内俟斤”为小可汗。在处罗可汗失败后,莫何可汗始大,“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诸国悉附之。”可见当时铁勒分为两支,一支是契苾部首领契苾哥楞率领,一支为薛延陀首领乙失钵率领。

根据《旧唐书》说法:“自突厥强盛,铁勒诸郡分散,众渐寡弱。至武德初,有薛延陀、契苾、回纥、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部、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霫等,散在碛北。”又《新唐书》称薛延陀“在铁勒诸部最雄张”)可见当时薛延陀部是铁勒诸部中最强盛,其自称本来姓薛氏,其先祖击灭延陀部,拥有其众,因此号薛延陀部,而《新唐书》指出薛延陀“姓一利咥氏。”不管如何,薛延陀本为铁勒诸部之一,且为其中强大一部,故后来在东突厥汗国崩溃后能够接替成为草原霸主。

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一下薛延陀的兴起,我们介绍一下突厥政权内部的事。而处罗可汗的故事是这样的,当时西突厥谢匮可汗得到隋炀帝支持,于是出兵攻打处罗可汗,处罗可汗战败而走,于是入于隋朝,东突厥阿波系突厥就此断绝。后来东突厥始毕可汗(启民可汗之子)于武德二年(619)派使者至长安,遂索杀此位处罗可汗。谢匮可汗是西突厥历史上的一代明君,当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朝于隋,被隋朝拘留,西突厥人于是拥立曷娑那可汗的叔父,是为谢匮可汗。后来隋炀帝西巡,想要让东突厥阿波系的泥撅处罗可汗来相会(也就是表示臣服),而处罗可汗推辞不肯,于是隋炀帝听从裴矩之策,让谢匮可汗击败了处罗可汗,被迫来朝见隋炀帝,从而被隋炀帝带着到处走。而谢匮可汗则于大业十一年(或许是没有收到消息,又或者是感念炀帝恩德,要知道这时候隋朝已是强弩之末,外强中干),“遣其犹子,率西蕃诸胡朝贡”。在谢匮可汗时期,由于西突厥势力强盛,于是薛延陀、契苾二部又去可汗之号臣服于西突厥(“及射匮可汗兵复振,薛延陀、契苾二部并去可汗之号以臣之。”)谢匮可汗于大业十三年去世,之后即位的是其弟统叶护可汗,又是一代明君,史载:“统叶护勇而有谋,北并铁勒,控弦数十万,据乌孙故地,又移庭于石国北千泉;西域诸国皆臣之,叶护各遣吐屯监之,督其征赋。”《旧唐书》甚至说:“西戎之盛,未之有也。”统叶护可汗时期不仅让西域臣服,并且征收其赋税,还北并铁勒,可能又吞并了一些铁勒的部族。但是大体上隋唐之际铁勒部出现东西分属的现象,“回纥等六部在郁督军山者,东属于始毕,乙失钵所部在金山者,西臣于叶护。”可见铁勒回纥部是属东突厥,而薛延陀是属西突厥。

东突厥汗国的崩溃和薛延陀汗国的诞生
东突厥汗国的崩溃是薛延陀壮大的客观原因,所谓一废一兴。而其中薛延陀部本属于西突厥,又为何能在东突厥汗国瓦解之际接替霸权呢?
首先是薛延陀的东迁。上文所说西突厥谢匮可汗、统叶护可汗时期,铁勒诸部是服从于西突厥汗国的,然而此时西突厥汗国内部又爆发内乱,《旧唐书》记载:“贞观二年,叶护可汗死,其国大乱。乙失钵之孙曰夷男。率其部落七万馀家附于突厥。”可见当时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死亡后,西突厥国中打乱,乙失钵的孙子夷男率领其部众七万余家投靠东突厥。其实这件事是这样的,当时西突厥汗国的统叶护可汗被其伯父莫贺咄杀害,莫贺咄自立为大可汗,非法的上位手段加上莫贺咄本为西突厥的小可汗,并无威望,于是“国人不附”,于是弩失毕部率先反叛,推举泥孰莫贺设为大可汗,而泥熟不从,迎接流亡在康居的统叶护之子咥力特勒,将其拥立为可汗,是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肆叶护可汗),双方“连兵不息”,西突厥的附属国纷纷背叛。早在之前就有统叶护可汗“自负强盛,无恩于国,部众咸怨,歌逻禄种多叛之”的事件,而此时爆发的内乱又导致铁勒诸部(也薛延陀为主)的反叛,所谓“其西域诸国及铁勒先役属于西突厥者,悉叛之,国内虚耗。”薛延陀东迁就是这样的背景,是年为贞观二年。
其次是东突厥汗国的内乱。在西突厥汗国内乱的同时,东突厥汗国也不遑多让,阿史那氏为首的突厥诸部内乱不断,原来的汗位继承人(东突厥处罗可汗之子郁射设)投降于唐朝,许多突厥部落纷纷投降唐朝,而突厥属部也选择起义反叛,贞观元年(627)五月,突厥大行台苑君璋投降唐廷,贞观二年四月,契丹酋长摩会率部投降唐廷,且之后唐朝攻灭了突厥扶持的梁师都,而位于漠北的回纥等六部(包括在附属于东突厥的东支薛延陀部)不晚于贞观元年(627)已反抗东突厥(实际上根据《旧唐书·阿史那杜尔》的记载:“武德九年,延陀、回纥等诸部皆叛,攻破欲谷设,社尔击之,复为延陀所败。”武德九年即626年,可见当时欲谷已经兵败,接着阿史那社尔也兵败,而同卷记载,阿史那社尔“年十一,以智勇称于本蕃,拜为拓设,建牙于碛北,与欲谷设分统铁勒、纥骨、同罗等诸部。”这两人的战败意味着东突厥汗国对诸属部控制的瓦解)。东迁的薛延陀部也许在此时也跟着举起义旗,也就是张公谨说的:“又其别部同罗、仆骨、回纥、延陀之类,并自立君长,将图反噬,此则众叛于下”,可见当时起义规模之大,此外张公谨说的“拓设出讨,匹马不归;欲谷丧师,立足无地,此则兵挫将败”,“欲谷丧师”是指因回纥起兵,“突厥颉利可汗遣子欲谷设率十万骑讨之。菩萨领骑五千与战,破之于马鬣山。因逐北至于天山,又进击,大破之,俘其部众,回纥由是大振。”回纥首领菩萨以五千骑兵大破突厥十万骑兵,是为东突厥一大挫折,又击败前去讨伐的突利可汗(始毕可汗之子),其人被突利“轻骑奔还。颉利怒,拘之十馀日”,然而正如张公谨所说的,当时反抗东突厥的铁勒各部“自立君长”,没有统一指挥,而薛延陀逐渐赢得了漠北诸部的归心,如史载薛延陀首领夷男“遇颉利之政衰,夷男率其徒属反攻颉利,大破之。于是颉利部诸姓多叛颉利,归于夷男,共推为主,夷男不敢当。”而又有记载贞观二年时,唐太宗派遣乔师望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纛”,借助唐朝声势,加上夷男得到漠北诸部的拥戴(可能与其率众七万东归,加上祖父乙失钵曾为铁勒的可汗有关),遂成为漠北的霸主,贞观三年,薛延陀正式称可汗与漠北,派遣使者朝贡唐廷。《旧唐书》记载:“夷男大喜,遣使贡方物,复建牙于大漠之北郁督军山下,在京师西北六千里。东至靺鞨,西至叶护,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大部落皆属焉”,而其中的回纥部菩萨虽然以少胜多,且与薛延陀并列为铁勒强盛部落,也“因率其众附于薛延陀”,此外如突厥别部的车鼻,本来也是阿史那氏,被北荒诸部推举为大可汗,但是“遇薛延陀为可汗,车鼻不敢当,遂率所部归于延陀。”可见当时夷男赢得漠北诸部拥戴,在大漠以北,西域以东的地区建立了绝对的威权,而东突厥颉利可汗仅仅拥有漠南一地,东突厥汗国已经瓦解,而之后唐军李靖等于贞观三年(629)十一月出击,次年四月颉利可汗被押往长安,东突厥汗国灭亡,漠南地空,至此,薛延陀可汗成为草原上唯一霸主,因此有“东至室韦,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临瀚海,即古匈奴之故地。胜兵二十万,立其二子为南北部。”的记载,虽然比之东突厥控弦百万仍有不及,但也为势力强大。

薛延陀汗国的发展
薛延陀汗国是建立在唐初铁勒诸部反抗突厥的背景下的,仅仅铁勒诸部就有十余部落,而其中回纥部又颇为强盛,加上投降的突厥部落(如车鼻可汗,还有“颉利之败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来降者甚众”的记载,可见投降薛延陀的突厥部落必然为数不少),其根基较为东突厥汗国并不更稳定,反而有更脆弱的嫌疑(比如《册府元龟》中记载唐太宗问其:“自算何如颉利之众”),虽然无法得知唐廷在薛延陀崛起这件事上起到了多大作用,但是薛延陀赢得漠北诸部归心无论是借助了唐廷声望还是追认事实(夷男自称:“我本铁勒之小帅也,天子立我为可汗”),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仰赖大国承认,也为后来薛延陀汗国的瓦解埋下祸根(见后文)。
此后薛延陀汗国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击败了肆叶护可汗和阿史那社尔的入侵。上文已述阿史那社尔的事迹,在镇压铁勒诸部的起义失败后,阿史那社尔于贞观二年(629)“遂率其馀众保于西偏,依可汗浮图”,此时颉利可汗尚未失国,但是阿史那社尔的行为也暗喻着东突厥汗国的瓦解,在颉利可汗于贞观四年被送往长安,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再恢复东突厥汗国很有困难(面对着薛延陀汗国和唐朝的双重夹击),因此向西进发是好的选择。

而当时西突厥汗国还处于内乱之中(应该是指当时西突厥肆叶护可汗和权臣泥熟的斗争。上文已述莫贺咄与肆叶护的争斗,最终由于肆叶护可汗是原来大可汗统叶护之子,是为正统所在,加上统叶护本身也很有威望,所以弑君者莫贺咄很快就败亡,贞观四年(630)年左右,肆叶护统一了西突厥汗国。(《通典》:肆叶护既是旧主之子,为众心所归,其西面都陆可汗及莫贺咄可汗二部豪帅,多来附之。又兴兵以击莫贺咄,莫贺咄大败,遁于金山,寻为咄陆可汗所害,国人乃奉肆叶护为大可汗。)肆叶护成为大可汗后,遂决定恢复其父的伟业,征伐叛逆的铁勒诸部,“大发兵北征铁勒,薛延陀逆击之,反为所败”,所谓“大发兵”可见当时的肆叶护必定是举行了一次规模不小的征伐,但是被薛延陀部击败,也说明当时薛延陀汗国处于朝气阶段,势头正盛。而肆叶护为人“性猜狠信谗,无统驭之略。”杀了功劳最多的乙利小可汗,而且是没有什么理由就将其族灭,以至于“群下震骇,莫能自固”,又猜忌泥熟(本来当初就是要拥立他),于是泥熟跑到焉耆国居住,而肆叶护的暴行导致“其后设卑达官与突厥弩矢毕二部豪帅潜谋击之”,肆叶护轻骑逃往康居,不久后死去,于是泥熟可汗被拥立,是为咄陆可汗。而大概就是在这段内乱时期阿史那社尔向西迁移(即所谓“后遇颉利灭,而西蕃叶护又死,奚利邲咄陆可汗兄弟争国”),阿史那杜尔扬言要投降,“因袭破古蕃,半有其国,得众十馀万,自称都布可汗。”战胜了西突厥后,阿史那杜尔决定向北进发,将矛头对准了薛延陀部,他对手下诸部说:“首为背叛破我国者,延陀之罪也。今我据有西方,大得兵马,不平延陀而取安乐,是忘先可汗,为不孝也。若天令不捷,死亦无恨。”其手下诸酋长说:“今新得西方,须留镇压。若即弃去,远击延陀,只恐叶护子孙必来复国。”然而阿史那社尔执意不从,亲自率领五万骑兵讨伐薛延陀于碛北,当时连兵百余日,相持不下,此时咥利始可汗(即泥熟)为唐太宗派刘善册立,“社尔部兵又苦久役,多委之逃”,薛延陀部乘机击败之,阿史那社尔逃亡到高昌,只剩下万余军队,又与西突厥交恶,于是于贞观九年(635)投降于唐朝,由此再无人挑战薛延陀汗国地位。

再说薛延陀汗国与唐朝的关系。虽然夷男帮助唐朝弄垮了东突厥汗国,但是随着薛延陀部的兴起,唐太宗又“以其强盛,恐为后患”,于贞观十二年(638)册立夷男二子为小可汗,所谓“外示优崇,实欲分其势也。”可见其猜忌之心。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唐太宗将突厥各部安排在河套之地(即所谓河南地),之后向东西扩展,西至西域边缘,东至辽东。在贞观十三年(639),唐以阿史那思摩为可汗,让其率领河南突厥诸部返回河北,也就是安置在漠南一带,此举大概出自经费和安全因素考虑,然而此举引起薛延陀的不满,史称:“会朝廷立李思摩为可汗,处其部众于漠南之地。夷男心恶思摩,甚不悦。”双方爆发冲突显现,不过阿史那思摩直到贞观十五年正月才正式率领部落渡河。
《太平御览》引《唐书》记载:“贞观中,弥泥孰可汗李思摩部落济河,于故定襄城为牙帐,户三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思摩之初建也,诏锡其土,南至大河,北有白道川。而白道牧田处龙荒之最,突厥咸竞其利。思摩以北接延陀,种落初集,其力尚微,未敢北徙,至是始还其国。因上言曰:‘非分蒙恩,立为落长,实望子孙竭诚奉国,作国家一狗,北门守吠。若延陀侵逼,请家口徙入长城。’诏许之。”根据这个记载来看,当时阿史那思摩有户三万,兵四万,马九万匹,相比于“胜兵二十万”的薛延陀汗国确实显得弱小,又从原文中“思摩以北接延陀,种落初集,其力尚微,未敢北徙,至是始还其国。”以及其自言:“若延陀侵逼,请家口徙入长城。”可见当时阿史那思摩思考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应对薛延陀汗国的压力。
果不其然,很快薛延陀于贞观十五年十一月就发兵南下,“北狄铁勒薛延陀,发同罗、仆骨、回纥等众,合二十万,度汉,屯白道川。据善阳岭,以击突厥可汗李思摩之部。”(《太平御览》引《唐书》)根据上文薛延陀汗国不过有兵二十万,此次又动员“同罗、仆骨、回纥等众”,达到二十万兵力,多少有点倾巢而出的意味,即爆发著名的诺真水之战。此战无论是《新唐书》《旧唐书》还是《通典》《册府元龟》《唐会要》都记载为二十万,然而实际上的参战兵力并不多,薛延陀本部大概有八万人,而实际上与唐军交战的大度设(夷男之子)只有三万骑兵。此次入侵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真珠可汗(即夷男)听说唐太宗打算东封泰山,跟手下说:“天子封泰山,士马皆从,边境必虚,我以此时取思摩,如拉朽耳。”其中有偷袭空虚的唐朝之意。唐太宗击败薛延陀后,责让真珠可汗说:“语尔可汗,延陀为大,突厥为小,尔责突厥羊马,又勒首领侍卫”,而薛延陀南下的理由是“突厥部数窃羊马”,当时薛延陀意图让突厥臣服的目的,也许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也是其率兵南下的原因,至于所谓盗窃风波,估计也是借口。
不过即使这样,阿史那思摩自然不是对手,于是引众撤退到朔州,留下精锐骑兵迎战。而唐朝为了援助东突厥,出动了大军。《资治通鉴》记载:“(十一月)癸酉,上命营州都督张俭帅所部骑兵及奚、契丹压其东境;以兵部尚书李世勣为朔州道行军总管,将兵六万,骑千二百,屯羽方;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将兵四万,骑五千,屯灵武;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将兵一万七千,为庆州道行军总管,出云中;凉州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出其西。”可见当时唐朝出动了12.32万兵力,以著名名将李勣为朔方方向的主帅,加上契丹和奚人的军队,规模相当之大。唐太宗在诸将出发之前告诫说:“延陀负其兵力,逾漠而来,经途数千,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其掩思摩,不能疾击。思摩既入长城,又不能速退。吾先敕思摩烧剃杀草,延陀粮食日尽,野无所获。顷者侦人来云,其马啮啖林木,枝皮略尽。卿等掎角思摩,不须前战,俟其将退,一时奋击,制胜之举也。”可见当时薛延陀大军犯了远道而来,在突厥部落坚壁清野的情况下,又面临补给不足的缺陷,唐军准备抓住薛延陀将要撤退的时机一举胜之。
薛延陀汗国之前击败西突厥的入侵和阿史那社尔都是依靠步兵,于是这次来打仗先在国内讲武,让他们学习步战,每五个人为一个小组,其中一个久习战阵的控制马匹,其余四个人向前步兵作战,打赢了就骑着马追击,如此战术颇为奇葩。而且用刑颇为严酷,所谓“失于应接,罪至于死,没其家口,以赏战人,至是遂行其法。”这种战术被唐军针对性打击。当时大度设率领三万骑兵逼近长城,想要进击突厥,但是突厥已经逃走,于是让人登上长城大骂,恰逢李勣的大军赶来,大度设自知不是对手,于是率领其部众从赤柯泺向北撤退,李勣选麾下及突厥精锐骑兵六千从直道来截击,越过白道川在青山一带追上大度设,大度设跑了几天,到达诺真水,决定率领军队还击,列阵十里。当时突厥军队先和薛延陀军队一接触,结果战不利,引兵撤退,薛延陀军队乘机进攻,遇到李勣率领的唐军迎击,薛延陀军队万箭齐发,唐军战马被射伤,李勣下令唐军下马步战,以长槊兵数百列阵,一起向前冲击,击溃了薛延陀的军队,而副总管薛万彻已率领数千骑兵提前袭击了控制马匹的“执马者”,“其众失马,莫知所从,因击之,乃大败。”由此诺真水战役唐军大胜。“《旧唐书·李勣传》作“虏五万余计”,《太宗纪》《北狄铁勒传》《薛万彻传》以及《册府元龟》载“斩首三千余级,获马万五千匹”(陈星宇《唐与薛延陀诺真水之战真实战况考略》)而经过陈星宇考证认为“唐军战果仅为‘斩首三千余’”,吴玉贵也认为:“汉文载籍中虽然对这次胜利大肆张扬,但实际上薛延陀在大漠南北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

在诺真水大战后,薛延陀和唐朝关系又有所缓和,真珠可汗请求和突厥保持友好,又于贞观十六年九月派遣其叔父沙钵罗泥敦策斤来请婚,献马三千匹,唐太宗问房玄龄说:“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崛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唯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灭除凶丑,百年无事,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亦足三十年安静,此亦一策也。未知何者为先?”唐太宗思考两策,一为出击,二为和亲,房玄龄回答说:“今大乱之后,疮痍未复,且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主张和亲,于是唐太宗说:“朕为苍生父母,茍可以利之,岂惜一女?”决定和亲,准备把第十五女新兴公主嫁给真珠可汗。然而实际上阴谋颇多,按照唐太宗说法,真珠可汗这么渴求和亲是因为:“薛延陀所以匍匐稽颡,惟我所欲,不敢骄慢者,以新为君长,杂姓非其种族,欲假中国之势以威服之耳。彼同罗、仆骨、回纥等十馀部,兵各数万,并力攻之,立可破灭,所以不敢发者,畏中国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国之婿,杂姓谁敢不服!”考虑薛延陀汗国立国不稳,又新遭大败,想要迎娶大唐公主的目的也许正如唐太宗所说是假唐朝威势震慑各部。夷男也说:“我本铁勒之小帅也,天子立我为可汗,今复嫁我公主,车驾亲至灵州,斯亦足矣!”可见“铁勒之小帅”并不能脱离唐朝的帮忙。双方约定在灵州会面。然而此次和亲实际上毫无成果,史载:“薛延陀先无库厩,真珠调敛诸部,复,往返万里,道涉沙碛,无水草,耗死将半,失期不至”,结果只是白白折腾,之后唐太宗下诏取消婚姻。
但薛延陀并没有停止对于突厥部的压力。贞观十六年何力部不顾原来首领的反对全部北降薛延陀,通过“时薛延陀强盛,契苾部落皆愿从之”的记载来看,薛延陀汗国当时仍非常强大且具有吸引力。在贞观十六年的婚姻事件后,“李思摩数遣兵侵掠之。延陀复遣突利失击思摩,至定襄,抄掠而去。太宗遣英国公李勣援之,见虏已出塞而还。太宗以其数与思摩交兵,玺书责让之。”当时薛延陀汗国和北返的突厥各部始终争斗不息,这是矛盾所在,到贞观十九年,北返的突厥各部最终顶不住压力尽数南还,请居内地,薛延陀汗国还是最终取得了胜利。当唐太宗于贞观十九年举行东征高丽的大战役时,还不让派遣使者警告薛延陀说:“语尔可汗,我父子并东征高丽,汝若能寇边者,但当来也!”真珠可汗并没有硬气,而是派遣使者致谢,还请求发兵助军,之后高丽大败于唐军之手,高丽权臣莫离支许诺重利来希望真珠可汗发兵相助,夷男也不敢轻动。唐太宗得知后淡淡地对近臣说了一句:“以我量之,延陀其死矣。”当时左右近臣皆不解其意,后世司马光也大感疑惑:“按太宗虽明,安能料薛延陀之死!”其实不难理解,薛延陀当时虽然比不上唐朝国力强大,但绝无如此怯弱之理,唯一解释是真珠可汗当时病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于是采取稳健的政策,因此唐太宗也推测出来真珠可汗状态不对。不久后真珠可汗(即夷男)去世,是为薛延陀汗国第一代君主,也是在位时期最长的君主。
在他死后不久,薛延陀汗国就土崩瓦解,走向灭亡。
薛延陀汗国的崩溃和灭亡
虽然薛延陀成功地将东突厥部落逼回了河套地区,但薛延陀却很快进入了分裂局面。吕思勉曾评价突厥汗国说:“盖突厥部族,本不甚大,赖铁勒归附,又乘乱招致华人,并抚纳西胡,以成其大。然大矣而本不固,故一朝失政,即土崩瓦解也。”(《隋唐五代史》)而突厥汗国尚且如此,薛延陀汗国又能如何?薛延陀汗国本身比东突厥汗国更加不稳定,甚至没有达到东突厥汗国时期的地位(比如多次与北返的突厥部落作斗争,虽然最后成功,但是也反应出其在漠南地区的控制力并无东突厥之强),而陈星宇曾评价说:“唐初铁勒诸部反抗突厥的统治,建立了薛延陀汗国,实际上这个政权是十余个铁勒部落合并而成的,‘突厥已亡,惟回纥与薛延陀为最雄强’,只因夷男为乙失钵可汗之孙,家室显赫,具有较强的号召力,才被推举为漠北共主,一旦薛延陀宗族核心发生内乱,将无力镇抚回纥等强大的铁勒部落,汗国必然失去对漠北草原各部落的控制力,‘彼同罗、仆骨等十余部落,兵可数万,足制延陀’,而这些部落此时已经具备了同薛延陀统治核心分庭抗礼的实力。”可见当时薛延陀汗国本身立国未稳,铁勒诸部为突厥压榨,最终叛逃,又形成联盟击败东突厥汗国,而在此背景下成立了薛延陀汗国,并非薛延陀部族本身能够制衡整个草原,可谓立国根基不稳,加上此时爆发的薛延陀汗国统治层的内乱,就进一步导致了薛延陀汗国的灭亡。

一开始夷男(真珠毗伽可汗)任命庶子曳莽为突利失可汗,统治东方,而嫡子拔灼为肆叶护可汗,统治西方,也是传统游牧帝国的三部分(左翼、中间,右翼),而那次入侵(诺真水之战)就是曳莽建议的,由此“国人多怨”,于是在葬礼上,拔灼分兵赶回将其杀害,并且自立为颉利俱利失薛沙多弥可汗,而这时候唐太宗还在征伐辽东的高丽,于是拔灼乘机南下,因唐朝已有防备,遂引兵北撤。而拔灼统治期间也不算稳定,史载其“多杀父时贵臣而任所亲昵,国人不安”,“多所诛杀,人不自安”,看起来是想建立自己一套班子,但是因为诛杀过多,导致局面相当不稳。而薛延陀的阿波设在靺鞨东境遇到唐朝使者,小战不利,回来散布恐慌说:“唐兵至矣”,点燃了柴火,“众大扰,诸部遂溃”。
多弥可汗仅仅带着十多名骑兵(也有数千名骑兵之说)逃跑,投靠阿史那时健,但不久被回纥所杀,宗族被灭,其地盘也被夺走。薛延陀部剩下部众五六万人奔往西域一带,拥立了真珠毗伽可汗的弟弟的儿子咄摩支,是为伊特勿失可汗,他派遣使者来对唐朝说:“愿保郁督军山。”而唐太宗下诏让兵部尚书崔敦礼和李勣去招抚,提出了“降则抚之,叛则击之。”铁勒诸部一向臣服于薛延陀部,这时候听说咄摩支到来都非常惊慌,唐太宗“更遣李世勣与九姓敕勒共图之”,
而李勣到达后,咄摩支表面上表示要祈求投降,背地里准备抵抗唐军(一说他想要投降,但是部众持两端),被李勣得知后,遂一举击败,史称:“斩五千馀级,系老孺三万,遂灭其国”(其年为贞观二十年,是为646年)。而薛延陀最后一任可汗咄摩支本来逃匿于荒谷之中,最后在唐朝招抚之下投降,送往长安,被拜为右武卫大将军。贞观二十二年,契苾、回纥等十多个铁勒部落因为薛延陀帝国的瓦解,称:“薛延陀不事大国,暴虐无道,不能与奴等为主,自取败死,部落鸟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分,扶问翻。不从薛延陀去,归命天子。”于是相继投降唐朝,唐太宗“因其地土,择其部落,置为州府”,其中“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仆骨为金徽都督府,多览葛为燕然都督府,拔野古部为幽陵都督府,同罗部为龟林都督府,思结部为卢山都督府,浑部为皋兰州,斛薛部为高阙州,奚结部为鸡鹿州,阿跌部为鸡田州,契苾部为榆溪州,思结别部为蹛林州,白霫部为置颜州,凡一十三州。拜其酋长为都督、刺史,给玄金鱼以为符信,又置燕然都护以统之。”(《旧唐书》)唐太宗由此羁縻漠北各部,也可以算是开疆(),由此薛延陀汗国灭亡。

如此庞大的帝国就这样土崩瓦解,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芝兰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