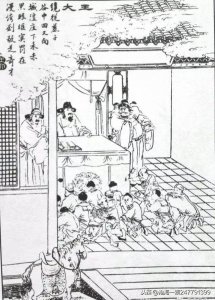加缪《局外人》:人生缺乏“仪式感”,是罪过,还是幸福?
张爱玲说:“生活需要仪式感,仪式感能唤起我们对内心自我的尊重,也让我们更好的,更认真的,去过属于我们生命里的每一天。”
人生在世,仪式感能让我们单调的生活不再乏味、枯燥,甚至是更精致。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仪式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调味剂。比如情人节的一顿烛光晚餐,再比如生日会精心制作的小惊喜。
我们时常遇到的情况是,男人不解风情,女人苦叹生活没有“仪式感”。于是,这段感情就在平淡中默默消沉,不欢而散。“仪式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分分钟会肢解掉一段美丽而凄婉的爱情。
早在1942年,法国作家加缪就深谙此理。他的成名作《局外人》刻画的就是一个因为缺失“仪式感”而获罪判刑的人物--默尔索。由于在母亲葬礼上没有表露出悲伤的“仪式感”,主人公默尔索成为世人眼中“罪大恶极”的死刑犯。

加缪
一、生活中的局外人,仪式上的旁观者
什么是仪式感?法国童话故事《小王子》是这样阐述的: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
在《局外人》中,主人公默尔索的每一天都过得平淡如水,没有任何涟漪。对默尔索而言,生活没有变化,就是最好的安排。他感情漠然,面对亲情、爱情、友情都缺乏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
母亲死了,哭不哭无所谓;与女友玛丽交往,爱不爱无所谓;与邻居雷蒙相处,成不成朋友,也无所谓。任由外界生离死别,大喜大悲,都无法撼动默尔索静止而冷寂的心。
01、没有眼泪的葬礼,是悲剧的导火索
小说开篇就奠定了故事的悲剧性--“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
面对母亲的离世,默尔索的表现不像一个儿子,更像是一个旁观者。收到讣告时,他异常冷静。没有丧失至亲的悲伤,更多的是无奈和烦闷。
因为,为了赶赴养老院守灵,配合这次关于死亡的仪式,默尔索不得不向苛刻的老板启齿请假,不得不向朋友艾玛尼埃尔借黑色领带与丧事臂章,而这些琐事都让他厌烦极了。

去到养老院,他第一时间不是探望去世的母亲,而是与养老院院长交涉。他婉拒瞻仰母亲的遗容,欣然同意尽早下葬母亲的建议,毫无留恋之情;同时,他还果断接受门房端来的牛奶咖啡,在母亲的遗体面前抽烟打瞌睡,也毫无敬畏之意。
在旁人看来,默尔索的行径冷漠怪异。他在守灵仪式上的表现,没有一点诚意,更没有任何温情,仿佛躺在棺木里的那个人不是他的母亲,而是一只猫、一只狗、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相比之下,母亲的院友们更适合参加这场葬礼,更符合送葬的“仪式感”。他们纷纷前来,排成一队,有满脸愁容的,有细声哭泣的,更有悲恸欲绝的。
比如,母亲在养老院的伴侣贝雷兹就显得十分上心,他已经年迈不能参加殡葬了,还执意跟随殡葬队去送母亲的最后一程。瘸脚的贝雷兹抄了许多次的近路,为的是能够赶上殡葬队伍。
“贝雷兹最后在村口追上我们时的那张面孔。他又激动又难过,大颗大颗的眼泪在脸颊上,但由于脸上皱纹密布,眼泪竟流不动,时而扩散,时而汇聚,在那张已经变形的脸上铺陈为一片水光。”
年迈悲伤的贝雷兹,行动神态完全符合一个葬礼的仪式需求。相反,“冷漠的儿子”默尔索却缺少了仪式上应有的悲哀与愁绪。

02、没有承诺的感情,仍存仁义与善良
葬礼过后的第二天,默尔索一如既往享受他的周六。他在游泳时遇到了以前心仪的同事玛丽,并且与她看了一场费尔南德的电影。他的心情丝毫不受母亲葬礼的影响,照常谈恋爱,交朋友。
爱人,是可谈可不谈的。与玛丽陷入狂热的爱情中,在玛丽问起他是否爱着自己时,默尔索觉得这话毫无意义;朋友,是可做可不做的。当邻居雷蒙问他愿不愿意做他的朋友时,默尔索也是随意答之。
可贵的是,没有任何仪式感的爱情,玛丽仍旧爱着默尔索,没有任何仪式感的友情,雷蒙仍觉得这个朋友值得深交。对待爱情和友情,默尔索也如对待亲情那般随意,没有刻意的承诺,更没有精心的经营。但在关键时刻,他仍能够为朋友付出他所有的努力。
若不是那个星期天,他没有跟玛丽一起去游泳,没有与雷蒙结伴而行,更没有劝解雷蒙将手枪放在自己身上,也许就不会发生他糊里糊涂的杀人事件。被杀者跟默尔索无仇无怨,只因跟朋友雷蒙的过节,默尔索就认定了那是自己的敌人。
“仪式感”重要吗?不重要。默尔索的善良与仗义不需要任何形式上的承诺。但在世人看来,“仪式感”又很重要。默尔索过失杀人,最终演化为“罪不可赦”,只因他在母亲的葬礼没有表现出“如丧考妣”的悲痛。
在最后的判决中,朋友、爱人眼中善良、诚实、无害的默尔索,成为一个十恶不赦,人人得以诛之的杀人狂魔。缺乏生活“仪式感”的他遭受了斩首示众的责罚,并且是以法兰西人民的民义判处他死刑。
正如默尔索所感受的,司法调查一开始关注的并不是命案本身,而是专门针对他这个人。他们给这样一个淡然超脱、安守本分的小职员挂上“毫无人性”与“叛离社会”的名头。判定的依据竟是默尔索为母亲守灵时抽了一根烟、喝了一杯咖啡以及无法说出母亲的具体岁数。多么荒谬的逻辑推理,多么荒诞的司法怪圈。

二、狱中的呐喊,是荒诞人自我意识的觉醒
讽刺的是,在武断的判决后,神甫竟然多次前往监狱,企图用忏悔的“仪式感”来让默尔索相信上帝,皈依上帝。然而,教人向善的上帝并不关注随意把人妖魔化的司法怪圈,更不去揭发法律机制对人精神及道德上的践踏与残杀,反而来渡化深陷人性冤案的当事人。
形式化的皈依仪式,让默尔索感到可笑又可恨。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积聚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他发出了内心深处强烈而又顽强的呐喊。
“在我所度过的整个那段荒诞生活期间,一种阴暗的气息从我未来前途的深处向我扑面而来,它穿越了尚未来到的岁月,所到之处,使人们曾经向我建议的所有一切彼此之间不再有高下优劣的差别了,未来的生活也并不比我以往的生活更切实实在。”
自白中,默尔索质疑神甫,母亲的死、母亲的爱重要吗?别人尊奉的上帝,重要吗?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重要吗?希望嫁给我的玛丽与任何巴黎女人有区别吗?今天以后,玛丽重新找另一个默尔索,有什么重要吗?这些都不重要!

在即将死亡的默尔索看来,这个荒诞的世界中的一切没有任何区别,循规蹈矩的固化思想,已经让他感到深深的厌恶。在生命的尽头,他直面抨击了一切让他生厌的形式。
作者加缪曾说:“厌倦是有益的。因为,一切都始于意识,只有通过意识才有价值。这些见解毫不独特,但是显而易见:用在一时就足够了,正好可以粗略地辨识荒诞的根源。”
默尔索排斥一切“仪式化”的事物,对母亲的丧礼感到厌烦,对玛丽的爱情逼问感到厌恶,最后,对神甫的“谆谆教诲”感到愤怒。这一切的“厌倦感”恰巧是默尔索辨识世界荒诞的根源。
意识到世界的荒诞,默尔索便不上诉了。他已经坦然了,他意识到今天的死去与几十年后的死去,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任何英雄主义,默尔索却做出一个英雄应有的姿态,英勇赴死。
没有“仪式感”的默尔索,是世人眼中的荒诞人。在荒诞人默尔索的眼中,充满“仪式感”的世界是个荒诞的世界。
荒诞无所不在,它是我们生活的基本存在状态。放诸当下,一方面,我们渴望着未来的理想化状态,希望光辉的未来能够赶紧来到,另一方面,我们又恐惧未来时间的快速推移,生命的衰老与死亡。生命中处处充满矛盾的异殊感,这便是荒诞。
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异殊,造成存在的荒诞。当意识到荒诞,人就觉醒了,而一旦觉醒,他便时时刻刻感受到世界的陌生性、非人性以及非理性,在这种离异感中,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我消亡”。默尔索最终决定光辉地死去,正是他反抗荒诞的意识崛起。

三、“恋世”而不“厌世”,荒诞亦是幸福
荷马史诗中,有个叫西西弗的神话人物。西西弗泄露了宙斯掳走河神伊索普斯女儿的秘密,宙斯就派死神将西西弗押下地狱。没想到,足智多谋的西西弗用计锁住死神,从而导致人间许多年都没有人死去。人间混乱,诸神将西西弗打入冥界。
在打入冥界之前,西西弗立下遗嘱,要求妻子不要埋葬他的尸体。到了冥界,聪明的西西弗又告诉冥后说,一个没有被埋葬过的人是没有资格待在冥界的,同时请求给予他三天假期回去交代自己的后事。
更没想到,西西弗回到人间,重睹人世的面貌,感受到水和阳光、灼热的石头和大海,他就流连忘返,不愿回去那昏暗的地狱了。
等到他死去,诸神判处西西弗到地狱的另一边接受重重的刑罚,即每天要把一块沉重的大石头推到陡峭的山上,在那座陡山上,西西弗永远地做着同一个动作。
诸神对西西弗的惩罚,既无用而又无望。但在加缪看来,西西弗是一个荒诞的英雄。加缪认为,西西弗鄙视诸神,仇恨死亡,热爱生活,这就使他遭受了不可名状的酷刑,这就是热爱这片土地必须付出的代价。

神话中的英雄极具悲壮。这种悲壮与默尔索在狱中发出的悲壮呐喊有着同样的道理。他们同样罹难重重,却有着高尚的灵魂。他们共同鄙视着这个荒诞的世界,又保持着高度的清醒。他们既是不幸的,又是幸福的。
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曾说:“幸福和荒诞是同一片大地的孪生子。”言外之意,世界的荒诞感完全有可能诞生于幸福。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许许多多的人都跟西西弗那样,天天劳作,日日受苦,仍旧还享受着这个重复而又枯燥的生活带来的乐趣,这是荒诞的,无意义的,也是幸福的。
荒诞的英雄西西弗为人类的命运谋幸福,而勤奋努力的我们,也在辛苦工作中求幸福。而《局外人》中的默尔索也是如此,他断然拒绝了无谓的“仪式感”,在即将死去之时仍对这个世界存有留恋,他能够清醒地意识到世界的荒谬性,以“赴死”去追寻生命的意义,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尼采说:“重要的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恒的活力。”
人生如此短暂,没有连续永恒,但正因为它的无意义与荒诞性就更值得一过。从世界无意义的一种哲学出发,最终为世界找到一种意义和一种深度。
生命无需形式化的“仪式感”,只有认清荒诞的现实,坚持这种对峙状态,才能时时刻刻紧绷着意识,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反抗的激情热焰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