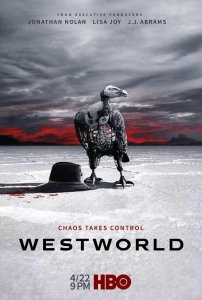“古惑仔”电影的意识形态读解
“古惑仔”一词属于粤语,泛指小流氓、小混混、黑社会小喽罗等。“古惑”一词正文应该是“蛊惑”,该等影片的编剧在写作之时避繁就简,用了与“蛊”同音的“古”字,由此“古惑仔”一词沿用至今[1]。
1996-2000年,根据《古惑仔》漫画改编的古惑仔系列电影一共十部,其中以陈浩南、山鸡等人为主角,演绎陈浩南“发家史”的古惑仔“正传”包括《古惑仔之人在江湖》(1996)、《古惑仔2之猛龙过江》(1996)、《古惑仔3之只手遮天》(1996)、《97古惑仔之战无不胜》(1997)、《98古惑仔之龙争虎斗》(1998)、《古惑仔之胜者为王》(2000)六部。六部影片由文隽编剧、刘伟强导演,在内容上彼此延续,讲述陈浩南从古惑仔上位至铜锣湾堂主,直至成为洪兴社团接班人的故事。由六部正传衍生出来的古惑仔“外传”有《古惑仔情义篇之洪兴十三妹》(1998)、《古惑仔激情篇之洪兴大飞哥》(1999)两部,讲述的是古惑仔“正传”中两个配角十三妹与大飞的故事;《新古惑仔之少年激斗篇》(1998)作为古惑仔电影的“前传”,讲述陈浩南与山鸡等人少年时代的故事;《古惑仔友情岁月之山鸡故事》(2000)内容上讲属于古惑仔电影的“别传”,前半段讲述山鸡少年时代与邻家女相恋的故事,后半段重又回到江湖厮杀的套路中来。其它以古惑仔为题材仿拍跟风之作,除《洪兴仔之江湖大风暴》(1996)、《古惑女之决战江湖》(1996)等少数几部具有一定水准之外,其余大都粗制滥造。

在作为“正传”的六部古惑片中,主角陈浩南少年时代因不堪忍受欺负,加入洪兴社团做了古惑仔,其后,陈浩南与山鸡等好友不断受到来自都市江湖世界的考验,首集中为洪兴社团铲除篡位者靓坤,次集中与来自台湾三联帮的丁瑶斗智,第三集里和东星社团的乌鸦厮杀,到第四集山鸡与洪兴社内奸生蕃竞选,第五集陈浩南与东星司徒浩南单挑,第六集再赴台湾,与三联帮帮主之子雷复轰交锋。影片主角陈浩南、山鸡启用郑伊健和陈小春这两位当时的年轻偶像扮演,并对其进行商业包装,看上去别具魅力。古惑仔们身着奇装异服,举止放荡不羁,讲话粗口不断,处处惹是生非,这种种僭越社会规范的行为对于青少年来说,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古惑片“表面上是八十年代江湖片的复苏,也明显是一趟市场触觉的胜利——在幕前幕后皆现老化危机的芸芸港产片之中,以青春偶像搬演流行漫画故事,使人耳目一新。”[2]从市场运作来讲,古惑片显然是一次颇为成功的市场投机。制作者们看准了古惑仔漫画在青少年当中的流行畅销,瞅准商机,采用以往江湖片的模式,对其改头换面重新包装,把江湖片中的主角由心狠手辣的黑帮大哥换成初涉江湖的古惑青年,而后推向市场赚取利润。仅1996年这短短一年之内,便连拍三部,其市场运作之纯熟迅捷由此可见一斑。


福柯在他的文章《关于异类空间》(Of Other Spaces)一文中,曾提出“异类空间”(heterotopias)的概念,用来指称“一种处于边缘、颠覆的位置而同时又具备折射社会文化功能的空间”[3]。以下笔者将借用“异类空间”的概念以及福柯关于“异类空间”的理论,对古惑片中“都市江湖”的空间呈现进行研究读解。
按照福柯的观点,二十世纪是一个以空间为主导的时代,“历史”不再以线性的时序顺畅无阻的推演文明的前进,而是走向横切的空间。如果说进入1980年代,香港社会还依然能够享受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种种便利,并由此树立起自己本土化的自信与优越感的话,那么到了1980年代末,由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开始渐显,集体焦虑开始成为现代文明的顽疾弥漫于整个都市。由1986年《英雄本色》首创的“英雄片”应时而生,以一种将现代文明予以倒退的方式,将现代都市改造成为一处江湖空间,从而缝合了香港社会在时间上的裂隙。都市江湖的影像空间与香港观众的“江湖心理”暗合,共同建构了都市江湖的镜像空间,此亦成为寄生于香港警匪电影当中、为香港社会所独有的“异类空间”。

及至1990年代,“九七”问题成为一块阴云笼罩在香港都市的上空,构成香港市民巨大的心理压力。原本一往无前的现代文明,在时间刻度上被强行阻隔,刻度的另一端成为一片茫茫未知的真空地带。香港电影在此一境况之下,由时间的受阻而走向空间的自我沉溺。更加上1990年代后期香港社会的风云变幻,好莱坞电影的入侵、盗版业的摧残、东南亚电影市场的丧失,整个香港电影工业在1990年代后期几乎濒临死亡边缘。古惑片的骤然出现并大行其道,不能不说是以上诸多因素的合力结果。由时间上的茫然无措,香港警匪电影走向空间上的营造建构。英雄片中没落的、个体性的都市江湖,到古惑片中,发展为体制完备等级森严的江湖社团。由社团组成的江湖空间完全寄生于现代都市,并凭借着与现代都市发生关联——更多时候是在以收保护费等形式吸取都市的血液——而存在。通过将都市江湖改造成为帮会格局的社团形式,并将社团种种活动进行“仪式化”的包装,古惑片中的都市江湖成为香港社会更为完善的“异类空间”。恰是都市江湖这一空间上的自我完善,缓解了香港社会在1990年代后期时间上的巨大压力。临近九七,时间被压缩为令人窒息的平面,时间上的压迫唯有靠空间上的开掘才能够予以缓解,古惑片在1996年短短一年间连拍三部,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英雄片自1986年始、1992年终、长达六年之久的一个周期[4]。此一情况固然与商业电影对于利润的盲目追求休戚相关,然而从更深层面讲,却不能不归因于由时间进程受阻而产生的反馈效应。
由此,古惑片中的都市江湖既非武侠片中的世外桃源,亦非英雄片中的众神之殿,而是成为一处带有“反乌托邦”性质的儿童乐园。这恰是“异类空间”的本质之一。所谓“乌托邦”,它代表的是某一集体的美丽幻想,其时间向度必然指向未来。然而,“九七”回归这一时间上的断裂,必然将任何关于“乌托邦”的幻象予以驱散。在此一境况之下,古惑片中的都市江湖便作为香港社会乌托邦梦幻被粉碎后的一次反弹,成为渴望与梦想不能实现的别样表达。都市江湖作为一处“反乌托邦”性质的异类空间,营造出“讲义气”、当大哥、拿刀砍人等种种现代江湖中的生活状态,供观众徜徉其间予以自我麻醉。如果说英雄片是借没落的都市江湖来抒写现代文明当中失落已久的兄弟情义的话,那么,古惑片则是通过对江湖社团内部格局乐之不疲的精心建构,以及对古惑仔们向社团大哥位子奋斗的发家史的书写,来维系都市江湖作为“异类空间”的麻痹功能。就其实质而言,都市江湖的完善不过是现代文明进一步的倒退。作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的一股逆流,精心建构都市江湖的古惑片注定了其稍纵即逝的命运。古惑片在经历1996年的眩眼夺目之后,似烟花般迅即隐退,在短暂装点寂寥夜空之后,并未能够定格为璀璨繁星中的一颗。

一方面,古惑片中的都市江湖作为一处“偏离的异类空间”(heterotopias of deviation),折射出香港人的自我麻醉心理;另一方面,香港观众意识及潜意识里的种种幻象,亦在都市江湖的镜像空间中予以显现。古惑仔们奇装异服的打扮、粗口不断的俚语、持刀砍人的放纵行为,成为香港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影迷“从恶如崩”的最佳范本;而当上老大之后前呼后拥的风光、挥金如土的体面、一言九鼎的威严等等,更加迎合了男性影迷自我膨胀的心理。此外,影片当中不断将香港置于一个众星捧月的位置,洪兴社团出入台湾、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在与当地黑社会势力的交往中始终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这无疑是香港人一厢情愿的白日美梦。古惑片第六部《胜者为王》中,陈浩南以古惑仔的砍刀本领战胜日本剑道,更是荒诞到了幼稚可笑的地步。正是通过这种种简单低级的媚人桥断,古惑片中的都市江湖勉强维系并“恶意”捧吹着香港人妄自尊大的心理。香港观众于现实中积聚的种种失意挫折、焦躁不安、惶恐无奈,借古惑片中的都市江湖予以宣泄;同时,古惑片制作者们本着商业投机赚取利润的目的,刻意迎合并满足着观众的这样一种“期待心理”,从而使古惑片在缓解由时间阻隔所造成之集体心理压力的同时,成为1990年代末香港社会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一。


事实上,从英雄片开始,都市江湖作为一处异类空间,在承担社会功能的同时,便已经暗含着其潜在的“自取灭亡”的危机。都市江湖作为一处保守、落后的镜像空间,在缝合时间裂隙、宣泄集体焦虑、承担‘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功能的同时,缔造的却是与现代文明相背道而驰的主体。英雄片由于将影片主角设定为近乎于神的黑道英雄,都市江湖由之成为一个众神之殿,普通观众只能高山仰止未必能够模仿效尤。因此,这一暗含的矛盾尚不足以凸现出来;而在古惑片中,影片采用一种“伪纪实主义”的风格,将主角设定为生活于社会边缘的古惑仔,并将都市江湖改造为一处恣意妄为的儿童乐园,由此,都市江湖所暗含的危机开始暴露出来。相对于英雄片而言,古惑片这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询唤“主体”的功能无疑更为“卓越”,而为古惑片所询唤的“主体”,无非是一群妄自尊大、自我膨胀的“古惑青年”,此类“主体”虽更为适应“九七”之前倍感压抑的香港,然而对社会无疑具有更为巨大的危害潜质。古惑片在稳定现状的同时,却缔造出更大的社会危机,并将其延展至未来时空。
对于成年观众而言,古惑片所营造的都市江湖,无非是一个类似于电玩游戏的取乐把戏;而对于判断能力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影迷来讲,古惑片中的都市江湖却成为其偏离社会规范、滑向作奸犯科的最佳范本。如果说香港观众对于古惑片的喜爱,其实质乃是一种不自觉的饮鸩止渴,那么,古惑片的制作者们则是在“利”字当头的行事原则之下,成为1990年代末香港社会不自觉的“造鸩者”。事实上,从第四集开始,古惑片便已经被定级为三级片。究其原因,乃是因为古惑片中的都市江湖,在发挥其原初的抚慰、缓解、宣泄功能的同时,开始渐显其教唆、怂恿、缔造犯罪的潜在危害。此亦成为香港电影中的都市江湖在古惑片热潮尚未退却之时,便已开始呈现溃败解体之契机的重要原因。
[1] 列孚:《90年代香港电影概述》,载《当代电影》2002年第二期。
[2] 李焯桃:《古惑仔潮流与九七情结》,载《1996香港电影回顾》,登徒主编,香港电影评论学会,1997年。
[3] 【法】Michel Foucault:“Of Other Spaces”.Diacritics,16:1,1986,转引自洛枫《盛世边缘:香港电影的性别、特技与九七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文中提到“……福柯在列举不同空间的意义时,特别强调其中一种处于边缘、颠覆的位置而同时又具备折射社会文明功能的空间,成为‘异类空间’(heterotopias),这种‘异类空间’,其实亦是贯串福柯全文的主要理念。所谓‘异类空间’,属于外在性的,是人类生活不同的位置,也是空间与空间之间产生的不同关连,它与‘乌托邦’(utopia)一如孪生的镜像,是人类生活理想与现实冲突的反照,如果说‘乌托邦’是人类生活美好的渴望与想象的蓝图,那么,‘异类空间’便是这些渴望与想象不能实现的的现实处境。为了进一步解释‘异类空间’的特性,福柯提出了六项准则:第一,‘异类空间’是每个文化特有的存在模式……第二,每个‘异类空间’都具备不同的功用价值……第三,‘异类空间’常常与别的空间矛盾并存……第四,‘异类空间’也具有历史的‘时性’,称之为‘异类时性’(heterochronies),它能表达一个空间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五,‘异类空间’必须经由特定的‘仪式’才可进入或离去……第六,‘异类空间’必须与其它现存的空间发生关系才可存在……”
[4] 实际上,在六部古惑片中,只有在1996年拍摄制作的前三部才是真正的古惑仔电影,及至第四部《战无不胜》,主角陈浩南已经由古惑仔上位到了铜锣湾老大,并开始对社团生活感到些微的厌倦。有趣的是,在第五部《龙争虎斗》和第六部《胜者为王》中,陈浩南对于社团生活的厌倦重又一扫而光,影片继续建构着古惑片中“讲义气”、通过奋斗当老大等价值认同,因此,古惑片到第四部以后,已经纯属商业电影的狗尾续貂之作。